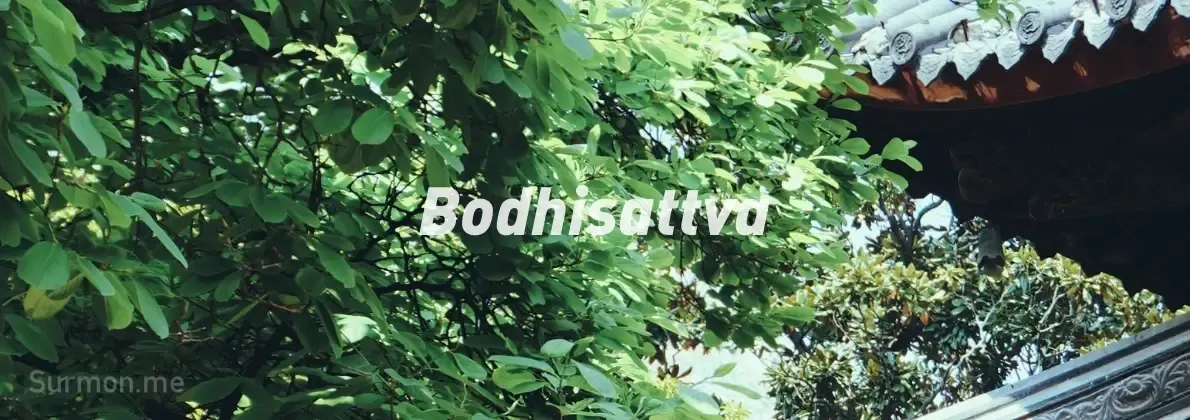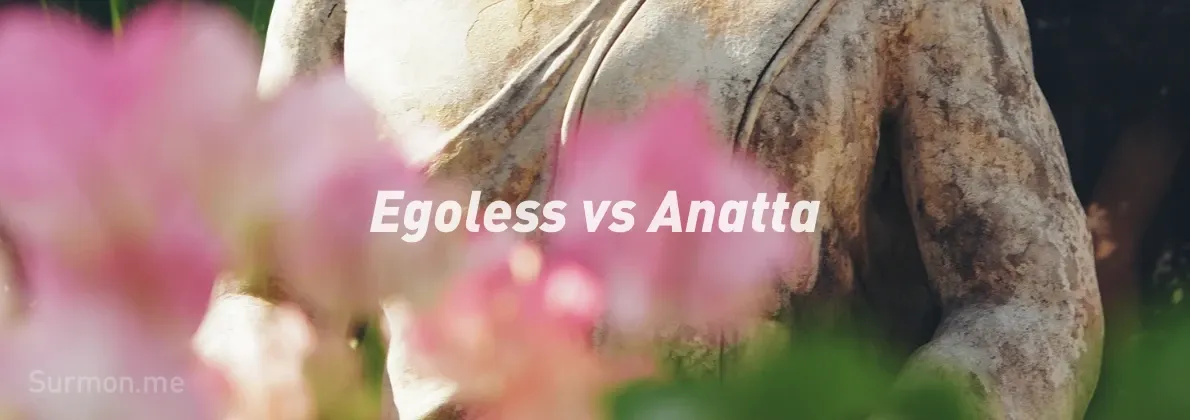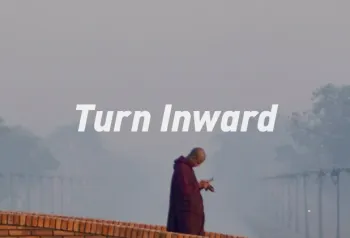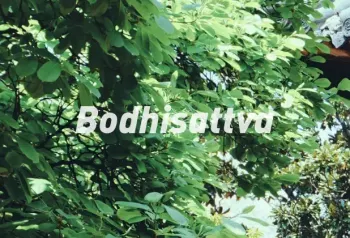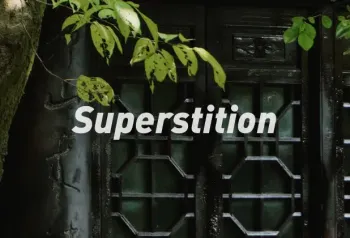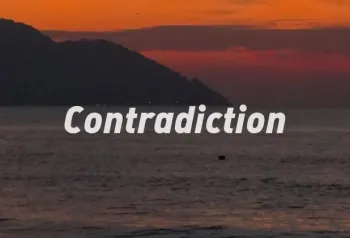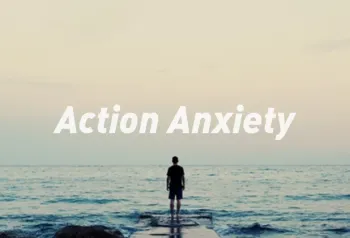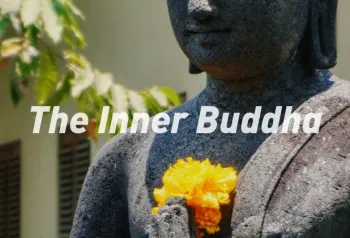2026 年 2 月 21 日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日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1
thread14 小时前
thread3 天前
去厨房洗个碗,我们都会下意识地先放碗碟,再打开水,再抹上洗洁精。
或者,我们总是会先扫地,再拖地,再用纸巾拾起最后一点点碎屑。
就像我们算一个普通的乘除法,都会从后往前一个个位进地计算一样。
其实数字领域的一切事情几乎都可以拆解成这样经验的一种实践,像是 TCP 的三次握手、卷积网络的层层分解、Skills 对 SOP 理念的应用。
技术并没有发明新的逻辑,它只是把人类在物理世界里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有效生存经验,用更精确、更稳定、更可重复的数学和代码重新描述了一遍。
边界更复杂,是因为数字世界可以容纳近乎无限的并行和交互,但底层逻辑依然是经验的结晶,它永远都是可解释的。
虽然可解释,但不是总被理解。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边界不一样,创造者和使用者的角色也不一样。
所以也可以认为:AI 在某种程度上,学习了那些最为聪明和智慧的人类所产生的高密度经验,但面向所有人类分发。
作为人类,需要接受经验边界变模糊、主体性危机,这件事。
但如果你还是在认为 AI 创造 = 我创造。那会很荒谬,你也会越来越痛苦。
-
尽量,别去成为什么,只是利用,和经受它。
这样能对生命最大化负责。
thread3 天前
最佳实践其实总有一个隐性条件:相对性。
也就是当下的特定规模、特定需要、特定团队、特定技术栈,在这些特定条件下的最优解。
如果是个人项目,它的相对性就来自:这个人的审美、偏好、强迫症。
这些东西,才是推动重构与设计的重要力量。
总是追求事事绝对的最佳实践,也是一种技术精神病。
这种病,会让发布延期,让创业失败。
说的就是我。
thread4 天前
thread4 天前
和 Gemini / GPT 连续聊了一个多月技术,聊了数据库设计、OAuth 实现、AI Agent 的架构和调优,聊了很多,比连续 5 年来线下交流的技术总和都多。
在以前,工程师的经验很重要,经验是靠实践积累来的,人是经验的载体,所以工程师很值钱。
现在,经验本身已经被海量的数据训练代替了,这种代替几乎是超越任何人类经验的代替,也就意味着经验变得廉价了。
人人都可以在很短暂的一个个瞬间,习得从未有过的经验,成为高手;甚至确切地说,人成了经验的工具,人成了模型的工具。
人变廉价,其实是经验变廉价了。
没变廉价的东西,还有,但是变少了,比如:情怀、审美、非效率的追求、不求意义的坚持。
thread6 天前
我想,也许没有耐心是正常的。
对一类事情厌倦了,就没有动机参与了。
如果外部的压迫并没有消失,自然会想果决地做些什么。
要去做些什么的时候,动机又出现了。
哪怕这个动机,只是为了杀掉动机。
thread6 天前
死亡,或者面对死亡,是一种体验。
没有概念和文字能概括这种体验,就像其他的体验一样。一被表达,它就崩塌了。
试着别再去分析,不再追逐一个确定精准的名词,就能离「存在」更接近一些。
所以,你看,在「存在」的维度,交流哪有存在的必要性;没有,多余的。
动物就不需要语言,它没有效率,但也不需要效率,它就一直在那里「存在」着。
又想到佛陀。
佛陀是一位伟大的人,一位不普通的普通人。
thread1 周前
信息社会,这个词的意思是说,社会结构是由众多注意力编制而成的。
从古至今,注意力的形态从奢饰品一般的书籍,到现在无处不在的声光电。人们获取信息更容易了,但专注于信息的能力却越来越差了。
声光电本身并不廉价,从工业上它叫效率,从心理上它呈现为廉价。它既是一种系统层的进步,又是一种个体层面的贬值。
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方面在拼命剥夺人的注意力,一方面又非常需要有专注力的人。
不被打扰,主动地拒绝被打扰,才是最昂贵、宝贵、无价的品质。这种宝贵不是为了获得成就或产生价值,就只是为了把生命活好本身,也需要专注。
这并不是说必须要刻意安排一段时间去阅读或者做什么事。而只是,在那些习以为常的「无聊」瞬间,不再去打开社交媒体,不再去刷短视频,就足够了。
信息社会不奖励注意力,而是消耗它。就像是,不断靠砍一刀得来的红包一定支付着远超红包的代价。
但,社会最终会向拥有注意力的人支付回报。
与其你现在想要点个赞或者收藏,倒不如暂时熄灭屏幕,放下手机,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一分钟就够。
thread1 周前
thread2 周前
thread2 周前
本来只想要补一点点墙漆,结果发现底层腻子也需要重刷,然后发现砖没砌好,最后发现大梁里的龙骨也弯了。
这就是大部分时候即兴重构的原始动机。
thread3 周前
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千里路的意思,是无数日月的饥、寒、暑、汗、波、折。
人在交流同一段符号,其实是交流对这段符号的体验,交流的是经验密度。
在体验未足够发生之前,符号只能制造共识,不能制造相遇。
这几乎注定了,大部分需要「被解释」的场景,解释都是无意义的。
thread3 周前
曾经,遇到过那么多,聪明理性的人、文艺感性的人、爱读书的人、爱思考的人、创造艺术或者欣赏艺术的人、或者有所成的人。
这些聪明的脑袋,把「可解释」当安全感,把「概念」当护盾。或者把「感受」当唯一,奉「体验」为信仰。
我看他们,很认真、努力、讲逻辑、头头是道。我听他们,讲故事、哭笑闹,津津有味。
但在这些生命身上,我完全看不到松动、好奇、自在、清澈。
从未见过,就像我从未清澈过一样,never。
把世俗谛奉为真理的人,没有那种清澈。只有一层又一层的防御、粉饰、表演、造作、确认。
我被那股向外的力量推得远远的,就像是住进了一个装满了名贵家具的房间,喘不过气。
无话可说,不是因为自我多膨胀。
只是因为,无话可说。
对于这个,装满意志,装满企图心的世界,疲惫了。
thread3 周前
thread1 个月前
相比于最强的推理模型,更重要的是那个值得放进去跑一遍的问题。
相比于最强的编程模型,更重要的是一个解决了真实痛点需求的点子。
相比于最强的视频生成模型,更重要的是一个能打动人心、让人产生共鸣的好故事。
这里,这些模型无法解决的东西,都需要时间,都需要思考,这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不是 AI 所能解决的问题。
thread1 个月前
thread1 个月前
极好的一集访谈(法布施)。
Sherry 和 仁波切都在各自的领域很专业,仁波切的逻辑、语言、用词、譬喻、概念表达都相当优秀。
大部分英文对白也都算通俗易懂,中文字幕做得也很严谨、准确。
总之:这集视频的质量又好又高。
thread1 个月前
如果把浩如烟海的巴利三藏接入 LLM 实现一个 RAG 会怎么样?
大概会实现一种事实上的「在线佛陀」,线下的善知识不再那么重要了,是良师还是邪师也没那么重要了。
如果再接入物理数据的采集,把每天听到的、看到的、说出的、做出的,都采集、计算,再做出评估和指导。
那就实现了现实意义上的「科幻」。其实现在的 Agent 就能做到了。
也就是奈飞泰国曾经拍过的一部电影,iBuddha。
点子真好。
连夜开发,明天上线,后天就去纳斯达克敲钟。
thread1 个月前
thread1 个月前
人们缺的不是最强的推理模型,而是值得放进去跑一遍的问题。
人们缺的也不是最强的编程模型,而是一个值得做出来推向市场解决某个实际需求的程序。
人们缺的更不是最强的视频生成模型,而是一个能打动人心,让人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的好故事。
这里人们真正缺乏的东西,都需要时间,都需要思考,这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不是 AI 所能解决的问题。
[3]thread1 个月前
Gemini 正在逆天地进行实时编码、运行、和通过调取 Google 的线上收录,来成就一个近乎 0 成本的 WEB AI 助理。
地球上没有第二家公司可以做到,因为没有第二个 Google。现在的 RAG 还是得要自己 Embeding,自己维护向量库,而如果是公共且 Web 的数据的话,Google 本身就可以一定程度代替这些。
效率很高,有点酷。
thread1 个月前
Google 的极客基因在 Gemini 里体现得很明确(相比于 ChatGPT 的话)。
关于语义正确、架构设计、解耦抽象的技术话题,GPT 简直像一个「技术上稚嫩、情绪上谄媚」的孩子。
thread1 个月前
GPT 现在最危险的就是:谄媚陷阱。
也就是:过度泛滥的情绪价值、无限消解的认知摩擦、无条件强化的自我叙事。
显性的胡说八道会被警惕,但隐性的谄媚,总会演变成温和又持续的精神麻醉。
不续费了,直到它成为一台真正冷漠的无情机器。
thread1 个月前
原创

从统计学习到通用智能中文
更重要的,不是对工具的掌握,而是「工具为何被需要」。
原创

2025 投资报告:走慢的路中文
不曲折、不取巧、不费神、不躁动的路
原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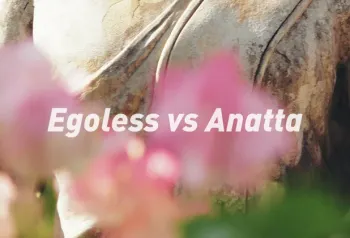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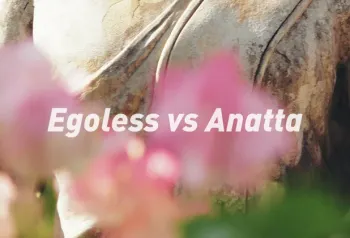
无我不是 Egoless中文
而是 Anatt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