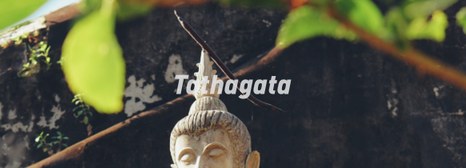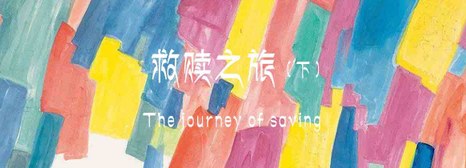原创
科学的尽头是态度

科学的尽头,不一定是神学,但一定会遇到一个叫「第一因」的终极障碍。
你可以制造一个无法再被解释的神,比如「上帝」。这是用人格化的第一因来回答问题。
也可以选择形而上的否定,比如「缘起性空」。这是直接消解问题本身,也就是所谓「第一因」本来就不存在,问题本身就是虚妄。
但无论是哪种回应,它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意识到了理性的边界,也意识到了这个边界的荒诞与无意义,它希望你放弃、接纳、臣服,臣服于某种更宏大的存在。
是放弃理性吗?不,是精神超越。
- 科学家在浩瀚宇宙前体会到敬畏。
- 有神论者在对神的信仰中找到了属于它的归宿和意义。
- 禅者安住于空性,收获了无边的自由和宁静。
科学的终点,啥也不是,是生命态度。
你说这算是答案吗?或者它有标准答案吗?
不,没有。
这是一个终极的、提供现实自洽的锚点,是不同个体面对生命根本困境时选择的姿态(态度)。 这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只要到达山顶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信仰」的核心含义。
那没有信仰的人呢?
没有信仰未必会疯,或者过得不好,但人人都逃不过生命终极的拷问。 拷问可能在默默无闻时,也可能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这对人人都公平。
真正重要的,或许并不是选择了哪条路,而是这条路是否能够真正融入生命、成为体验。
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思想家与圣贤,逻辑上自洽的理念很多,但只有那些能够被实践、被体证的,才能真正作用于人的内在,作用于生命,才有意义,才谈得上「开悟」。
不包含实践的理念,称之为精神娱乐更合适。 附庸风雅,或思想禁锢,又无意践行,那就是一场自我欺骗的闹剧,其实没有帮助,倒不如学点心理学来得实在。
真正那些在实践的人,那些把止观修完再来一遍又一遍的人,总是安静又认真地呆在丛林深处,沉默而专注。他们不需要,也不允许在社交媒体上自我标榜,更不会和别人争辩何为「开悟」。
真正的转变,不发生在言辞之中,尽管它们并不冲突。
(完)
期待你的捷足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