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不因恐惧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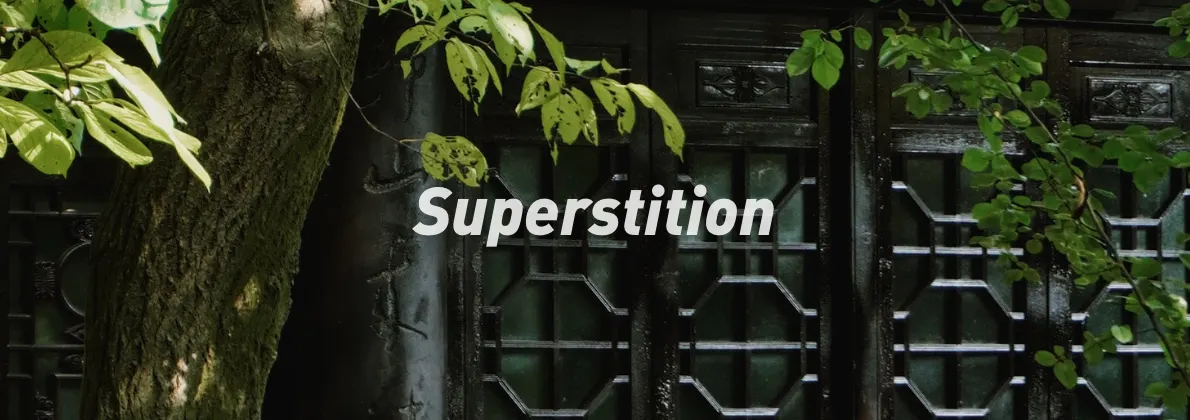
扪心自问,其实我在内心深处挺介意华人所说的「信佛」,特别是这个「信」字。从一开始到今天,从国内到东南亚,从出家到回家,这股情绪都没有改变。
也许这正是在说明这份修为还远不到家,自我还是那么炽盛。但没关系,我允许并承认这种情绪的发生,并且有义务去梳理和诠释它。
另一个个人原因是:不执着 ≠ 不作为。无论是否走在向内求的精神修行之道上,世俗责任始终在,无论这份责任是相对于有关系的人、陌生人、社会集体。
这个命题,无关乎某一乘或某一教法的差别,甚至与佛教本身都没什么关系。而是来自于宗教的运行方式:利用恐惧。
拿「信因果」来说。
最常见最普遍的信:相信这个世界在无法验证的地方运行着一套独立客观、绝对化、不可动摇的平衡法则,类似于因果报应积分系统,这套系统就像一只永远正义的无形之手悄然维持着某种现象关系的平衡。
就暂把这种无根之信称作「外在化因果」好了。这种信仰的根源,来自人对某种超越性秩序(或者说未知)的敬畏和恐惧(更多),以及对自身理性有限性(根器、认知等)的承认(或者说放弃)。
这种「信」确实可能导致一种「臣服」的发生,但它是以放弃自主思考和依赖为代价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中总能看到一些「走火入魔」的宗教现象:
- 因果被当做一种超自然的「报复」系统:你敢那么做,宇宙/神明就会惩罚你,我诅咒你下地狱!
- 因果被用于一种维护权威的统治工具:你敢质疑我/反对我/不按我说的做,你就会倒大霉。
- 因果被作为一种回避批评的万能借口:只要祭出「业力」大旗,就可以跳过所有理性辩论,直接从道德和超自然层面「消灭」反对的声音。
我倾向于把这种「信」称为:理性的脆弱和感性的巨婴。 凭完全主观的经验直觉观察,普遍 F 人和思考能力不好的人最容易走上这条路。这种信仰的第一动机,并非为了求得某种超越性的解脱或真理,而是为了逃避现实中无法排解的痛苦。
但第一动机就注定了它不能走到解脱之门吗?确实不是。西方的神学家 Augustine 就有过「恐惧是智慧之门」这样的观点。佛陀在《中部》 象跡喻經 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对老病死的恐惧正是出离修行的契机。
但,这里重要的点是:实际的成效,主要取决于信仰者的意图和实践,次要取决于外部社会(宗教)的环境,这两股因又是互相作用的。 外部环境部分,就是宗教的叙事和形式。也就是说:宗教的门开的有多大、有多偏,很大程度决定了它的整体认知环境、精神引导的阻力,和信众的最终导向。
据我所知,「地狱恐吓」与「功德交易」都不是佛陀所赞同和实践的。尽管佛陀住世时也曾多次以基于六道系统的「地狱叙事」来讲法,但要知道那是在极少数人受教育的古印度时期,知识的解释权被婆罗门完全垄断,尽管存在沙门思潮和六大派,但婆罗门主张的「轮回」叙事早已深入各阶层百姓的心。佛陀是利用当下环境的已有条件作为教学工具,佛陀的核心是基于「慈悲」的自由,而非基于「恐惧」的控制。
如果佛陀也是如前文的行事理念,就永远不会发生「央掘魔罗」转变为「不害」的心灵奇迹( 《中部》Aṅgulimāla Sutta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精神救赎也永远不会实现。对抗一定换来对抗,爱却有可能消解敌意。
如今的寺庙,摆各种神像来给信众拜,顺便还能扫码抽个签算个命,有的或许还有超度亡灵或灵位的业务,到底是「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还是「末法时代」?
这大概永远得不到答案,答案藏在人心深处的动机里。不是所有宗教都是如此,但在当下中国的宗教,事实一定可以用糟糕来形容,糟糕得多。
我的愚见是:今天的世界(中国)不适合方便法,越方便越下流,下流到最后是消亡,它正在恶性循环。 今日的香火依旧鼎盛,但那不再是追求或需求的鼎盛,而是欲望和痴妄的鼎盛。这样的鼎盛,就是法的衰败。
说另一种信:因果是心中的一种理念。 它可能更多来自无法被溯源的先天直觉,也或许结合了实际的生活经验。它类似于康德的「因果性为知性范畴」,或是「果报在自心」的直接体验,总归来说,它是一种基于自我认知的、主动选择的精神图腾。
在原始佛教或婆罗门教的起源中,它更类似于一种自然哲学理念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显化,它更接近于一种对现象规律的诠释,而非神灵审判。就把这种信称之为「内在化因果」好了。
这种理念,通俗地说:因果就是现象之间的互相作用。 一种现象作为一种力量,就一定会对其他现象产生作用,就像石头压在大地上一样,这是可以绝对确定的。而作为结果的现象同时又会对其他的现象产生影响,因产生果,果又作为因产生更多的果,因果之间就是「力」的流转。
「因果」的巴利语原词就是 kamma-vipāka,意思就是:业的结果。所以许多时候,Karma 本身就是因果的解释,也就是:现象之间的作用力。 在佛法的语境中「业」更多指向精神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许多场景下它涵盖了现代概念,如:潜意识、认知模式、情绪模式、心理惯性、心理障碍、心理创伤...
在这种情况下,「信因果」就不再是来自外在的压迫力量,而是自身主动行动、承担责任的可能性。 这时的「信」意味着承当、担当。只要能真正意识到「业」无时无刻、无边无际不在运行这个严肃的事实,就完全有动机、有可能通过禅修,或是实际上的积极作为去改变未来、扭转因果。这种心态下,没有抗拒、恐惧,也不等待来自外部的审判(事实反馈)。非常接近于禅宗的「不昧因果」。
展开来看:内在的果报在当下立即发生,作用会马上体现,具体就是精神状态的完成。 (积极的完成就类似于:平静、放松、坦荡、无愧、少执、无挂碍... 的情绪状态) 而外在的果报,会根据外在现象的时机和条件而作用。
比如,曾经被一个人重重地伤害,现在选择对这个人宽恕或是赶尽杀绝,都可以立即得到内在的一种完成。但在未来,无论是哪种选项,都会留下某种长久的作用力,比如可能发现自己的慈悲养出了祸害(产生了后悔),或者发现自己也许不需要那么决绝,应该给他人留下一种可能性(产生了内疚)。无论是哪一种,它都必定会在内部与外部,分别留下长久的作用力,这些作用力又会以无法预料的方式悄无声息地产生更多的作用力。
在这种认识下,对「造因」或者说「造业」是有发自内心的敬畏的,它需要以充分的诚实和严谨来面对自己的内在世界,同时也了解外部世界的控制边界(接近于不期待),它的底色是一种担当和责任感。
宗教的问题(坑)在哪呢?
宗教几乎总是无差别地先利用人性的恐惧,再重新疏导这份恐惧到自己想要的叙事逻辑中。(当然大部分时候宗教都是往积极超越的方向引导的,再没有追求的宗教起码也要与当下的伦理道德相匹配,不然也会慢慢被市场排除。)
这就导致了:宗教真的在事实上广泛地增强了人的依赖和愚昧。它即是方便之门,也是下流之门。 而根据我有限的经验来看,种种方便带来的副作用远大于作用。甚至不客气地说,在今天的世界里,这种精神依赖在不断地制造更多的心灵巨婴。
题外话:这样的论调有依据吗?今天的世界(中国)算怎样的世界?
在《长部》 Cakkavatti-sīhanāda Sutta 中有一个典故,基本上描述了一个社会从黄金时代走向泯灭是如何发生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导致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导致道德问题,道德的失控最终摧毁了社会秩序。
这里的秩序同时指物质秩序和精神秩序,更具体就是在说人群中贪欲、嗔害、杀戮、妄语的炽盛的程度,也可以直接翻译为过度的享乐主义、自我中心的泛滥、骗子伪大师的横行、广泛的戾气和攻击性。
如果一个社会中,语言摩擦变得很常见和敏感,人人随处随意的标签化,手握一颗颗断章取义的子弹。这几乎意味着沟通的桥梁断了,语言也不再是思想的载体,而是发射恶意之箭的弩。每个人都穿着无形的铠甲,举着盾牌,每一次对话都是一场攻防战。
总之,如果你只是如法行事,却总是感觉到如履薄冰,力不从心。那可能真的说明,这个地方就是快完蛋了,滴水不沾,油盐不进。它没有根基,正在精神等死。
这种情况怎么办?比较务实的做法是:认清现实,隐,或者逃。越远越好。
当然,这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在《法句经》或其他经典中,多有记载佛陀关于「默然」与「口业」的教导。具体每个人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
题外话:如果在现实中遇到前文所描述的「恐吓」人群,应该怎么做?
一、直接地意识到,这种行为属于「精神操控」,无论 TA 的动机和身份是什么。一位真正的修行人,也许会探讨、会辩论,或者会沉默,但绝不会恐吓。
二、避免辩论,迅速切断,避免无意义的注意力消耗。如果真的需要学习,那就另寻老师,或者,做自己的名师。
真正有力量的知识或智慧,从不需要依靠威胁来立足。
我清楚自己能力的边界,应该是永远无法比肩佛陀,所以我杜绝方便法。我不想不自知地自以为是,也不愿不经意地误人年华。
我只能亲力去做那些能做的、微不足道的。或在合适的时候告诉别人:蟑螂也是命,蚊子没有恶意,它也会痛,不至于判它死刑。永远说不出:今天你杀它,下次它杀你。 我只有这一种风格,也只会这一种风格。
话说回来,坑就在这里:宗教之所以为宗教,之所以是这种运作方式,之所以以这种复杂矛盾的面貌存在,很可能是因为符号化与简化是宗教传播的必然。如此表现,并不是宗教自身多强的主观意愿,而是人类拥有广泛的恐惧和脆弱,人类需要精神鸦片,几千年前需要,几千年后还会需要。
就像 以前写过的文字 :大部分人需要迷信,这是一个客观需求。没有正教就造邪教,总之必须有个强大的外来力量来被依赖才行。
从这个视角看,这些暗藏真理的宗教反倒真的成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存在。
回到问题,我还是介意别人上来问「你信佛啊」或者「某个高僧都塌了,你还信?」... 不仅是这,现在甚至听到「小乘」这个词语都有些坐难安。
佛陀住世时就说过 十事勿著 ,教导世人什么叫迷信与轻信。就算是无脑信,也该了解这最基本的教义,而不是轻率地把「信不信」当成社交货币。
而对于「小乘」这样的字眼,就像是太多的中国人对「支语」之类的词汇极度敏感,却又在无意识中每天都在重复「阿三」、「毛子」、「棒子」... 这些侮辱性词汇。
这在事实上,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认知挑衅。任何人都应该自发、严谨地为自身的言行、认知负责。
在以前,我总是耐心地回答:我在学习佛陀的教法(佛弟子),但不是迷信某种符号(宗教徒)。
现在,____。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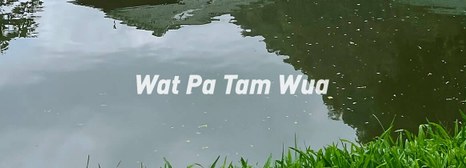





无意教化。